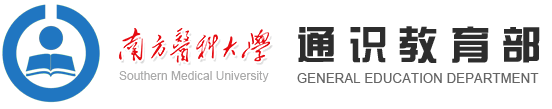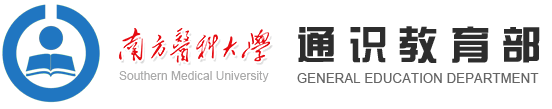10月30日,秋高气爽、万里无云,通识讲坛第七期活动于顺德校区学术会议厅开讲了。这期活动的讲座嘉宾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邓启耀教授。前两周,同学们对邓老师提供的两个备选主题进行了票选,“跨文化精神病学现象:说’蛊’”获得64%的同学睐,成为这一期讲座的主题。
讲座开场,邓老师风趣地表达了对医者的敬佩:“每天面对有病痛的人,能不受这些影响,健康而正常地活着、工作,只有心理很强大才做得到。”医生和人类学者其实有些共同之处,医生研究作为个体的病人的问题,人类学者关注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的病症。

由此,邓老师讲起一个社会现象——前几年在市场上热销的“巫毒娃娃”,据称用这种娃娃可以通过法术远程伤害和诅咒别人,以发泄怨气、不满,转移霉运。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和讨论。针对为“巫毒娃娃”辩护的网评,邓老师提问,“巫毒娃娃”没有严谨可考的背景与文化吗?“巫毒娃娃”只是玩具,不值得大惊小怪吗?用问题,引导同学们去了解巫蛊现象的历史渊源和现状,以及巫蛊心态。用一个个故事,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和思考。


热销的“巫毒娃娃”
典籍中的巫蛊与现实中的巫蛊
中国古代关于巫蛊现象的记载,可追溯到甲骨文、东巴文时期,各类正史、野史、笔记、方志、文学作品中都有其踪迹。以《史记》中记载的汉代“巫蛊之祸”为例,虽祸起宫廷权术争斗,但波及社会各阶层,据载2万多人因此丧命。再如,《红楼梦》中马道婆扎纸人做法害凤姐和宝玉的情节,针往纸人上一扎,宝凤二人就心口疼而发狂。可见,巫蛊现象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当代社会中巫蛊现象也一直存在。邓老师展示了他收集到的各种实例,比如,有网友家里装修时发现墙内嵌着贴有黄符的木剑(工匠厌镇之术);华南地区惊蛰“打小人”的习俗;巫蛊信仰中使用的纸马、恋药;描写蛊女后代的影视作品;关于巫蛊的学术研究和真实故事。
巫蛊信仰中使用的一种纸马
其中,最打动我的是两个关于巫蛊的真实故事,是邓老师的田野经历,他在《中国巫蛊考察》一书中也曾记述过。
一个故事发生在邓老师当知青时住的傣族村寨,当年寨子上有个姑娘,人长得秀气,又丰满,算是乡里一枝花,追她的小伙子很多。可不知什么时候起,人们忽然对她回避起来,背地里对她指指戳戳,轰传她是‘琵拍’(相当于汉族的“蛊女”)。知青们自不相信有“琵拍”,更不愿眼看这样一个姑娘被俗尚所坑,于是想打抱不平。据他们调查,被指为“琵拍”的人不敢走过晾衣绳,民间传说,只要一走过这绳子,“琵拍”就会现原形。知青们觉得,这无疑是攻破谣言的最好突破口。他们激动地策划着一次让科学与迷信较量的义举,然后满怀信心地去找那姑娘,只要她往这绳子下面一走,从此便不用害怕那些流言蜚语。然而,可悲、可叹的是,无论怎么劝说,那姑娘却不敢,在那样的文化心理场景中,她自己竟也相信了那谣传中的蛊女之名。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摩梭寨子,邓老师所在的民间传说调查队误入一个有“蛊”的人家,背负“有蛊”之名,在乡俗社会中是一种最可怕的压力。这一家人便像染上恶性传染病的人,被人人唾弃,孤独无助地被隔绝起来,到处是敌意,而对手是谁,却永远无法寻到。这家的小女儿也因此辍学,十几年后,即便她离开本乡本土多年,逃离了巫蛊之名的漩涡,成了一位妇女干部,但是一旦回乡,回到那种文化心理场景中,一切又都重演。只要她在这块土地上,那个无形而沉重的阴影,就将一直伴随着她。通过调研,邓老师推断,这家人的“蛊”,可能与这个母系大家庭的女主人曾在1958-1968那个年代当过生产队长,得罪过不少人有关。
邓老师意识到,蛊事实为人事的异化反映。巫蛊不仅仅是一种奇风异俗,只从“陋俗”、“邪教”之类民俗和政治概念,无法完全解释。他在《中国巫蛊考察》写到,“我所考查的这一文化的和心理的现象,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虚幻的现象。它是有形的、复杂社会的现实反映,也是无形的微妙心理的幻化投射。”从古到今,人们借此上演了一部部惨烈的悲剧、闹剧和丑剧,血泪凝成了一部部隐密的心史、情史和仇史,这部“书”永不会像摆得上架的那些“史册”那么引人瞩目,它只潜伏在那些巨著的字里行间,在坟墓中和民间传说中微露只言片语;它似乎永远只宜深埋在地下,深藏在人们心中,然而,一旦你能瞥它一眼,便再难忘掉。
巫蛊心态与极端信仰——非常意识状态与非常意识形态分析
邓老师分享了帮助一名自称“中蛊”的人进行“治疗”的故事,其间寻求过民俗、宗教等传统心理暗示的方法,后来诉诸现代医学精神病治疗方法。关于这例“巫蛊”病症案例的心理分析和精神病学的分析,对邓老师的研究产生了启发。“中蛊”的症状,符合跨文化精神病学描述的“非常意识状态”(non-ordinary State of Consciousness)的特征。从意志维度上看,患者有强烈的丧失自我控制的感觉而出现意志障碍。从知觉维度上看,患者的几乎所有感觉系统都有被歪曲或异化的趋向。从认知维度上看,尽管患者神志清醒,具有日常操作思维能力,甚至在思辩上反应敏捷,但是,在他身上并存着的几种认知系统中,各自的发展并不均衡,有的明显被强化或泛化了,有的又处于类似“前综合思维” 的混沌合一状态。
类似催眠状态、出神状态、销魂状态、入静、分离状态、附体体验、禅定、中邪(如“中蛊”)这样一些跨文化精神病症的专业或非专业概念,均可归到“非常意识状态”范畴。作为一种跨文化现象,它存在于几乎所有民族的疗病手段或宗教、精神生活中。
个体性的“非常意识状态” 最常见、为大量临床案例和科学研究所公认的诱因大致有两类,一为心理性诱因,一为药理性诱因。不过,邓老师认为如果仅仅以心理性诱因和药理性诱因来分析我们现在面临的群体性“非常意识状态”的疫情,似有不够。因此,他建议对“文化性诱因”予以关注。他认识“非常意识状态”在更多情况下是一种与传统意识形态或亚文化社会观念紧密联系的跨文化精神病理现象,而“巫蛊”这一文化话语更具有悠远的历史传统,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它在中国流传数千来,广布各地区各阶层,已形成自己独特的观念系统、组织系统、操作系统和符号系统。这意味着,精神病学意义上的“非常意识状态”,由于质、量、历史传承和现实影响等方面的原因,已具有了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非常“意识形态”或“文化心态”的某些特征。邓老师将其定义为“非常意识形态”(non-ordinary ideology),主要特指与主流文化的常规意识形态有所区别的一种亚文化观念体系或民俗化社会意识,其中文化性实践性因素和心理性精神性因素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正因为这个特点,它在很多时候,也深刻地影响着该社会的政治、宗教、哲学、道德、法律、文化和经济,影响着相当范围内人群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社会结构,成为一种具有潜在力量的社会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体系。一些“非常意识状态”已经深深地溶进我们的文化中,成为一种传统,成为一种依然影响着现世的社会性文化性疫情。
接下来,邓老师从人类学、跨文化精神病学双重视角归纳了“非常意识形态”的特点:思维异常与认知失序、行为异端与伦常失范、社会结构异态与人际关系脱失。
作为“未能结束的结语”,邓老师把抽象的理论分析与现实对接,提醒我们在社会出现危机、发生变革或转型中时,个体的“非常意识状态”和群体的“非常意识形态”,是很容易被激活的。它会激活某些破坏性很大的极端感情(如嫉妒、仇怨、悲观、冲动、偏执、浮躁等)、极端信仰和极端行为,激活一些人的阴暗心理和准黑巫术行为。一旦个人的变态适应了群体的需要,个体的“非常意识状态”也就很容易转化为群体的“非常意识形态”。回顾人类历史上、不同社会文化中,违反理性、违反人性的极端信仰并不罕见。通过考察和反思这些沉积了几千年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延续的东西,可以看到那些在“一定文化中体系性地隐藏着的东西”(法国人类学家古利奥尔所言)如何作用于人类的生活和心灵。
最后,邓老师分享了他受邀参加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世界精神病学协会跨文化分会国际会议的经历。随着全球社会的急剧变迁,关注文化与心理健康关系的文化精神医学日益受到重视。与此同时,中国的快速发展受到世界关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应对社会文化变迁挑战的经验,正在成为国际上行为科学、精神医学领域学者的热门话题。
在讲座尾声的自由问答环节,邓老师与来参加讲座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了愉快的对谈。
这次讲座不仅满是精彩生动的真实故事,还有跨学科、跨文化的不同视角,更有开放包容的讨论氛围。散场后,意犹未尽的同学们仍围着邓老师继续交流。